21 位摄影家镜头里的“中国事像"
上世纪80年开始,中国摄影在走出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模式和继而出现的形式主义的唯美之风之后,纪实摄影蓬勃兴起。在如今已经多样化的摄影格局中,纪实摄影仍然是非常厚重的一部分。《中国事像》收入了21位摄影家的纪实作品,这些摄影家大都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摄影发展的全部过程,他们用自己的观念、视角和语言表达对一个时代的个人关注和对纪实摄影的理解,他们的许多作品已成为我们关于中国当代摄影发展的记忆,如此规模的集合,足以让我们的观看成为一次对半个多世纪中国纪实摄影的回顾。
朱宪民是中国当代摄影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纪实摄影家,他早在70年代初期就开始关注平民百姓生活并且始终保持着一种平民姿态并具有鲜明的个人视点。他用三十年的时间拍摄黄河两岸,他的《黄河百姓》成为以影像方式全面表现‘黄河人’生存状态的、时间跨度最大的摄影专著。卡蒂埃·布列松书赠朱宪民:真理之眼,他永远向着生活。
就在朱宪民跋涉黄河的同时,于德水也以自己的方式把镜头锁定在中原地区的黄河两岸。他的拍摄着重于民间生活的日常性和民间生活的价值系统,他的画面充满着丰赡的人性,拙朴的乡风陶铸着具有拙朴乡风的摄影,他的思想不是沿着史诗的传统,而是沿着内倾的个人体验的传统,他的生性与经历形成了他的影像气质:平和、自然中执著不变,不动声色中潜藏激情,韧度与刚性中弥散的细腻与温柔。
闫新法拍摄于河南巩义的《皇陵百姓》以一种统一的符号化的方式,将这块土地的岁月断片统一在一种氛围和背景中,以整体的面貌,营造了略感冷清与静默的存在于历史表征中的现实情景,努力地让历史变得具体,变得鲜活,并且无处不在。他不断地提示着我们,那些在时间深处埋藏的,并不会真正的沉寂。那些被现实抛弃的,并不等于消逝。历史,需要永远地活在当下的现实之中,人,永远地需要保留对于历史的依赖或者是联系。
姜健以格式化的静态的语言,在具有象征意义和符号化的细节再现中,叙述着一个民族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文化景观。我们也可以根据他的照片了解到,城市化的进程也可以是一种城市生活意识与生活价值观向农村的扩散与渗透的过程。姜健在创作过程中力图把照相机面对世界的方式还原到人的眼睛直接面对世界的方式。姜健的眼光穿越镜头见证着他的“肖像”。读者对其“肖像”的阅读成为面对世界的持续见证。
赵震海同样把镜头对准了农村农民,但他有着更深一层的血脉情缘,他说我的父母和父母的父母都是农民,我没有理由不将镜头对准他们。摄影使他看到了更多的贫穷苦难,却只能感叹于影像的软弱无力,默默地承受内心的痛苦。他坚持用个性化创造去对抗影像的流俗与平庸,宁可被探索的失败击得粉碎也不愿被平庸拖沓得精疲力竭。赵震海带着执着甚至偏执把摄影融入生命。如今因患阿尔茨海默病(又称失智症)而失忆,但他的影响依在,这种影响既来自他的影像,也来自他的精神。
张惠宾的中原乡村体现为一种朴素化与微观化的社会采样,没有预设的、刻意的观念意图,放弃先在的、被赋予的理性判断。它以摄影家之“我见”,提供的只是有关中原农村生活的生动的视觉切片。它不主动去建构宏大意义与激情说教,因而有着更加客观与直接的真实。它不刻意地制造视觉冲击和情绪刺激,因而人物和场面鲜活有趣,体现出亲切的平视的视角和知识分子发乎本能的乡土关切。
秦军校长期关注乡土风俗民情特别是那些正在走向消亡的民俗,表现出一种民间文化情怀。他的拍摄采取了非常朴实的手法,掺和了一些自然主义的叙述语言。每一张对着镜头或是微笑、或是疑惑、或是不知所措甚至游移不定的脸,都是拍摄者“蓄谋已久”的精神定格,而这样一种“蓄谋已久”的过程恰恰又是拍摄者在这片生活了多少年的土地上耳濡目染甚至有着切肤之痛体验的结果。这样一种以生存体验为基本代价的纪实方式,是一种心灵与现实的直接对撞,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做作,因此才能显现出强有力的生命力。
马宏杰《中国人的家当》用有限度的静态照片来展示我们习以为常的大众生活,其中饱含着博物与文化之美、人类栖息多样性的哲学和作者借以烘托的新颖的艺术立意,反映出物质文化怎样通过个人物品体现,这些个人物品中包含了人的故事,有人的生活和命运,喜悦和心酸以及他们不断的失败和不懈的梦想。
周振华的摄影经历与大多数中国基层的摄影人一样,他们的摄影充分呈现了革命年代的话语方式。同时,在他们的经历中所呈现出的摄影人的热情、单纯、朴素,对于摄影如信仰般的虔诚以及摄影人相互之间真诚的友情,都是一个时代的印迹,是个体生命难得的财富。
王树洲用系统化的影像记录了20世纪70年代的辉县,呈现出一个逝去年代的中国农村的风貌,这些影像会激活我们的记忆,让我们再次面对昨天。虽然这些影像拍摄时已经被充分地意识形态化了,人物和场景大都进行过设计摆布,但是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和感受那个年代,作者的观看方式和表达方式与他的影像一起共同属于那个年代。
李江树有关北京的拍摄,更类似于一种苦恋式的都市乡愁——他深深怀恋着一座城,一座曾经像唐诗一样美丽的古城。在寻常巷陌,他为我们保留下最后的惊鸿一瞥——那些永远不可再现的生活场景,每一张图片都有着吹糠见米的思想质料与细节,凝聚着一个摄影人长达40年的、拍摄北京的心血和思考。
经过罗永进的去语境化处理,现实中的建筑演化成了一种非现实事物,就像一些布景里的东西,孤立地存在于城市空间中,或展示丑陋、或炫耀财富,或显示权力。通过对于一个又一个主题的全方位的关照与一种类型学式的执拗的编目与整理,罗永进建立起一种现实与观念形态的视觉联系。经由这些当代建筑,罗永进举重若轻地切入当代中国的城市现实,给出了一种令人措手不及的现实呈现。
王彤在十几年时间跑遍中国各地,将千城一面的“造城”运动记录在案。几乎所有的城市外观都似乎被一双无形之手化归一式。这种变化以一种不易察觉却翻天覆地的执着正将我们带入一种统一的城市景观丛林,并最终影响着我们关于城市的认知经验日益趋同。王彤以他敏锐而富于细节性的观察呈现了现实与历史暧昧交错中那一条隐藏着的牢固而紧密的精神牵连。
田野的镜头游走在城市同时也是乡村的边缘,他像一个勤力敏感的拾荒者,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小心翼翼地捡拾起被人遗忘的一个个记忆的碎片。每一个碎片都让人惊异,他隐遁在影像背后自己先战战兢兢地不让进入影像中的人或动物受到惊扰,但是他最后还是笃定地不露声色地成为了“他自己的”影像的主宰。疏离和寂寥的情绪贯穿在他的画面中,隐隐地刺痛观看者,同时也把观看者牵引向正在被淡忘的记忆深处。
王豫明一点点地放弃了纯粹的记录性视角,转而采用一种更加主观的方式和各种不寻常的角度。他的画面裁剪也不再那么“标准”,他“未对焦”的作品不再具有太多描述性效果,却更加容易唤起观者的共鸣。王豫明的禀赋和特质主要在于他能够捕捉周围世界中的美丽、悲怆和人性。他知道如何将这些直接表现出来,而不会采用很多浮夸和强调的手法。这是在他那双虽然不大,但是非常有活力和热情的眼中所看到的世界的表现。
牛国政的《练功》沉郁而生动、真实而荒诞。在他的镜头下,睡觉成了一种自以为是却又神秘莫测的生命意象,练功成了一种始于虔诚止于荒谬的宗教仪式。可以说,牛国政用细腻、偶然、突兀、疑问式的笔触赋予摄影另一种可能:摄影是一种提问的方式,而答案可能不在摄影中。牛国政以其独特敏锐的观察视角与丰富的影像采集记录了这段时期国人世俗生活的特殊表现,同时也成为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国人精神现实的有力表达。
余海波的影像给我们一个有质感的深圳,像被压路机压过了一样。这种被当作石子压进路面的质感,或许是1300万深圳人中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感。只有在深圳那些华丽的高楼的背影下,那些城乡结合部的嘈杂中,那些拥挤的宿舍和车间里,或许你才能触摸到它。在余海波的镜头里我们能够感觉到对生命的悲悯。
贾玉川游走在都市生活的底层,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弱势群体或特殊境遇者身上。他的拍摄基于对不同寻常的生命状态和生活方式的了解的欲望,他始终以一种尊重、平和、善意的态度走进一个个拍摄对象,他被一个个独特的生命所吸引,被强烈的探究欲望所驱动,在经年累月的追踪拍摄中,他身不由己地伸出援手,为改变他们的命运而努力,这为他的摄影赋予了真正的人文意义。
郭建设积攒了几十年的作品形成了一个内容充实、题材广泛、作品精良的图片库,这些图片跨越30年,记录了中国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的珍贵影像,堪称一部丰富多彩的现代历史画卷,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作为资深的经济媒体记者,王凡几乎接触到了所有如今已成为大佬级的当代中国企业家。《老板》采用介乎肖像照和生活照之间的影像关系构成模式,让被摄者完全处于自我存在状态,使其个性在松弛中彰显,同时摈弃被摄者所处场景中的任何象征、隐喻意味,最大限度地突出人物自身的性格特征,力求能够使之在欣赏者的审美互动中得到升华。如果说中国当代纪实摄影是众多摄影家共同参与的一部如《史记》般的宏大叙事巨著,那么,王凡的作品就是其中“财经本纪”的经典篇章。
罗勇的《大相中国》以现实的、具体的、微观的甚至是“碎片化”的日常细节,予以“全景敞视”式的呈现。也正是在这种超常景观的影像形式中,读者感受到了他长期历练下的控制与把握能力:场景、物体、空间与人物关系所形成的有效的图像结构,以及与主题的相互连涉关系。画面所渗透出的纪实影像的视觉魅力,带读者进入了当代中国市井现实的生活图景。
21位摄影家镜头里的《中国事像》是对中国半个多世纪社会历史进程的视觉书写和集体见证,也是中国纪实摄影发展嬗变的重要成果和探索足迹。
全视影像画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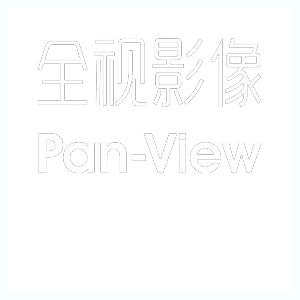

 豫公网安备 41019602002106号
豫公网安备 41019602002106号